讀書會消息:本周六 (20/7) 將舉行第二次筆友讀書會,今次會讀《一九八四》,詳情在文章最底。有興趣的筆友請在此報名。
讀魯迅的《野草》,雖不太習慣那麼花巧的散文詩格式,但也很有味道。可能因他「憤佬」的形象夠鮮明,或他那青春和熱情將逝未逝的曖昧狀態,我多少有同感。
其中有不少關於「希望」的篇幅,尤其有感。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這句摘自《野草》中的《希望》,原文出處據說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山多爾 (Petőfi Sándor) 的詩作,但我沒能查證到源頭。我對這句話有不少的體會,雖然覺得這些體會沒什麼實際用途。
我會說:希望與絕望本質相同,都是虛妄,也都是生活的基石。「信」與「望」的原理,都類似。
信
小時候學《聖經》,曾讀到出自《馬太福音》17章這樣的一句: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
我聽著導師們說這句話時,留意著他們的眼神;他們真的相信這話嗎?那是超自然的強大力量!我腦中想像的盡是大衛.高柏飛魔術表演的畫面:他雙眼緊閉、聚精匯神、左手食指輕輕搭在太陽穴上以增強專注力,額上彷彿還因太費勁而滴下一顆汗珠,然後猛然轉身舉高雙手,大喝一聲:「去!」,自由神像便在屏幕上消失無踪;還想起星球大戰中絕地武士用以隔空取物的宇宙原力,那和經文中講的信心,或者是指同一回事吧?
於是某次我騎單車經過吐靈港,遙望對面海那高聳入雲的馬鞍山山峰,我決定試一試心中有沒有種子般大的信心。我也聚精匯神,緊閉雙眼,像大便困難般用力閉氣,心裡默唸:掉!然後睜開眼。結果當然是什麼都沒發生。
那時年少無知,那種因簡單愚昧的信念而驅動的行為,回想起來甚為可笑。然而我想,「信」的本質大概也真是如此,雖然註定沒有結果,但人卻會因信而行動,耗盡青春,甚至一生;而那行動實實在在留下了生命的痕跡。信念最大的作用在行動本身,而非最終帶來那預期的結果。擁有堅強信念的人一般命途多舛,因為常因此做出有違常理、社會規範和法律的行為,且屢戰屢敗,自然要被體制和自然法則所懲罰。然而偶有實踐信念並僥幸成功的例子,如甘地、孟德拉等被後世所傳頌,成為信心的模範;但失敗的例子更多,而且同樣成為模範,那就是《聖經》希伯來書中列出的,所有因著信而行動,卻始終沒有如願的人。可見《聖經》所描述的信絕不只是怪力亂神,是我年少膚淺讀不懂,才會以為跟魔術一樣。
沒有信念的人,傾向穩穩陣陣渡過一生,或者循規蹈矩也是一種信念,較受控,較不會跳出框框。無可無不可,那也是人生的一種。
若說虛無飄渺的信念太離地,談「信用」便具體得多了。孔子說,民無信不立。一個無人信任的政府,執行什麼政策都事倍功半;一個誠信破產的人,能發揮的空間也很有限。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信把所有合作關係的力量放大,就如貨幣,人們信一元等於一元,是因為信政府、信制度,而不是因為一元真的等於一元 - 其實眾所周知,存款 100 元到銀行,銀行實際上只保留 10 元,甚至更低的金額在戶口,其他都用作投資用途;銀行在利用的是自己的「信用」。做生意貨到後可以一個月後才付款,而不用即時找數甚至先付款才等出貨,是因為信用。人與人之間肯敞開心扉交流,是因為信任。人夠膽把生命的安危託付給巴士司機和巴士,也因為信任。沒有信,連坐到椅子上也要猶豫,因為不肯定它夠不夠堅固。
然而,「信」的內容是一回事,所「信」之事實際上是否會發生或真實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前者引發各種積極的行動,所以是實在的;後者由於所信的往往不會實現或甚至根本純屬虛構,所以是虛妄的。
望
「希望」的本質,也跟信心相同。有時我覺得希望只是信心的延伸。因為有某種信念,例如信上帝存在並主宰一切,所以產生某種希望,例如公義遲早獲得彰顯,因為上帝憎惡罪惡。於是只要抱著希望,人就算處於惡劣的處境,也能積極地生活下去。
在英國曾跟一個來自巴基斯坦的移民閒談,提及香港的情況。他說,幾十年前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應該沒現在好?我說,沒錯,但那時人們對將來有希望。有希望,生活就有動力;沒希望,就算富足,也提不起勁。所以希望帶來的是生活的能量,而所望之事最終會否發生反是次要。
我最喜愛的翻譯小說《基度山恩仇記》的最後一句:
人類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這四個字裡面的:「等待」和「希望」!
總帶給我公義最後必勝的希望,那怕有生之年看不到,甚至惡人在世時沒報應,他們也會被地獄之火焚燒。我固然知道所希望的事情會發生的機率有多微小,但只要不放棄希望,便好像沒被擊倒,便會繼續行動。
青春總伴隨著希望,因為時間在年輕人那邊。然而當人漸老,情況便反過來。魯迅於《希望》一文中處處流露出這種歲月催人身心老去的感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而忽然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而絕望,本質上也跟希望相同,就是所絕之望實際上未必已絕,但哀莫大於心死,心死便不再追求,生活的動力消失,然後庸庸碌碌地等著滅亡。要完全摧毁一個人,剝奪他物理上的所有遠遠未夠,有時甚至會因此得反效果,因為受壓的人因此心無旁騖而變得更為堅定。摧毁一個人是要令他絕望,叫他死心,銷毁當下他為了未來而奮鬥的行動力,《一九八四》中思想警察對付異己的手段就是如此。
這也解釋了為何威權政府不怕自己表現得愚蠢和荒謬,有時甚至故意違反常理行事,因為要令大眾覺得理性和善美這些常識都不再適用,叫人對「明天會變好」死心絕望,以至連抵抗的行動力也喪失掉。
當信念和希望皆被摧毀,人的行動力便同時冰消瓦解,餘下最輕鬆的路,就是按已定下的遊戲規則生存;當信念和希望被重塑,人便會按著塑造的目的行動,那無關信念和希望最終是否真的會實現。中、英兩國在九七前給香港人民主的希望,不少人於是為此耗掉了廿幾年青春;現在民主的希望被政權以最誇張、粗暴的形式粉碎掉,絕望的人便停滯了。
我們能控制物質,因為我們控制了心靈。現實存在於顱骨之內。溫斯頓,你將會逐步學習。沒有我們做不到的事情。隱形,飄浮-任何事情。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像肥皂泡一樣從這個地板上飄起來。但我不願意,因為黨不希望這樣。
《一九八四》
信念和希望當然不只應用在那些宏大的政治理想。例如,一個人若對家庭的期望幻滅,那便不會再想為家人的未來而籌謀;對志業的理想幻滅,便不會再想在工作中追尋意義;對天國的憧憬幻滅,便不會再想祈禱。反過來,只要擁有信和望,無論環境多難,目標多不可能實現,甚至反過來說法多麼荒謬,人也能咬緊牙關堅持行動下去。信和望實在影響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只是我現在傾向相信那只是一種心理狀態。我早該領悟這一點的。
曾在友人的文章中讀到一句話,回頭竟已無法再在互聯網搜出來了。那句的大意是:
能帶出意義的,總是一個信念,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客觀事實。以「太陽在東邊升起」為信念是沒有意義的⋯⋯越是不信,越要深信。
寫得太好了,我一直牢牢記著,但今天我彷彿多了一點體會。我無法再深信自己可以叫馬鞍山跳進吐露港,或太陽應該從西邊升起;但我更了解那刻意選擇深信的信念,及那由此已生的對將來的希望,對我今天生活的實際意義是什麼。然而吊詭的是,一旦我更了解信與望的真像,要義無反顧地行動卻反而更難了。
讀書會
定時分享我讀的閱讀心得
以 Google Meet 進行,會議連結會在活動前以電郵通知。
每兩周一次,每次不多於一小時
英國時間周六早上 09:00,即香港時間下午 4:00
預設廣東話,若活動開始時有國語讀者在座,我會改以國語分享,但參與者如要發言請自由選用任何語言。
讀了書才來固然好;沒讀過但不怕雷(劇透)的,也無任歡迎;純粹借故來聊天,可能才是重點
下次活動
日期:2024年7月20日
時間:09:00 am (英國時間),即 4:00 pm(香港時間)
活動長度:1 小時
書名: 一九八四(購書連結)
作者:喬治.歐威爾
短評: 很多人只聽過《一九八四》的大名,及一些書中有名的概念如「老大哥在看著你」等,卻未必詳細讀過。今次我會嘗試用一小時討論一遍全書的重點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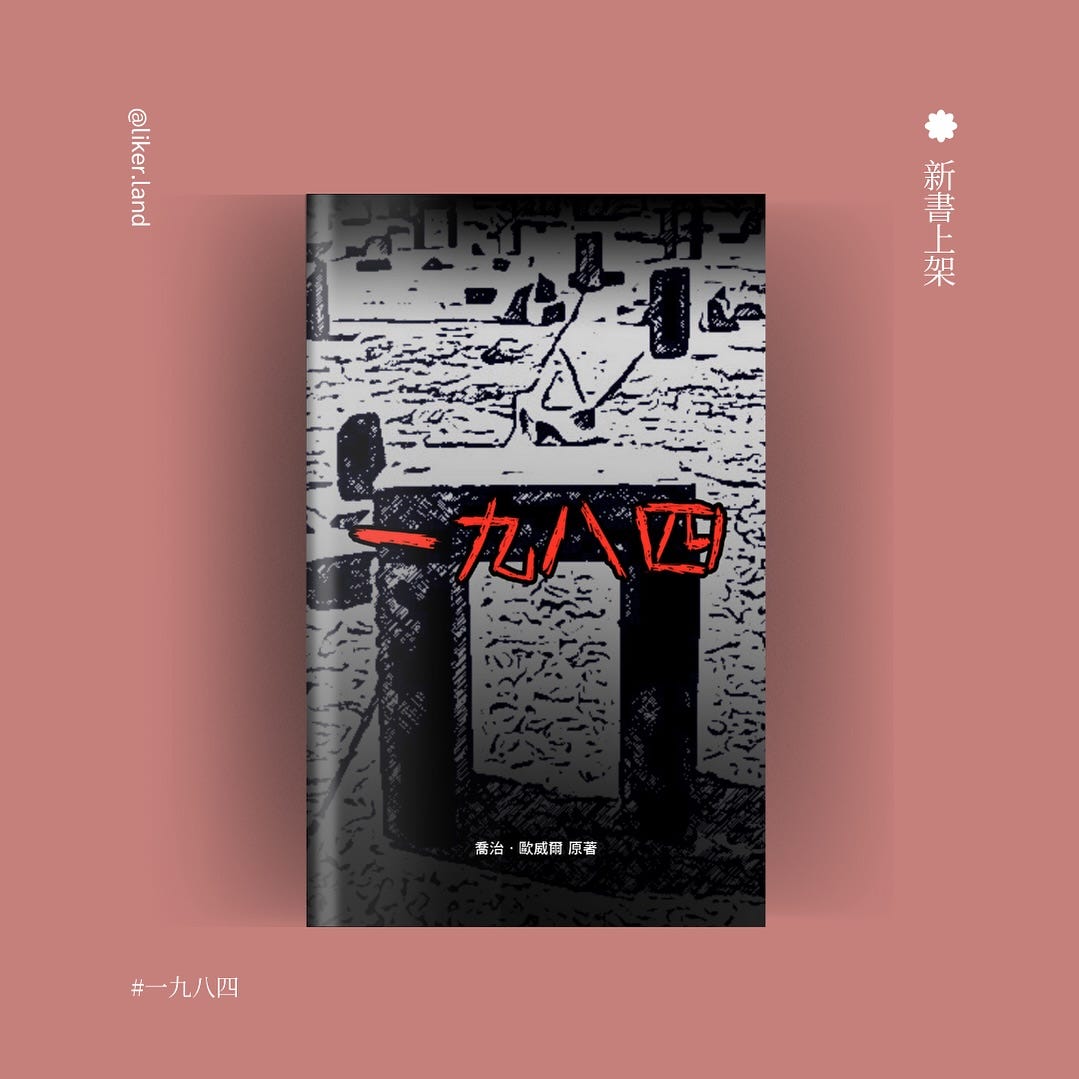

然而,能帶出意義的,總是一個信念,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客觀事實。以「太陽在東邊升起」為信念是沒有意義的。硬是要考究我們到底是否相信「好者有好報」的話,我會說,因為不信,所以相信。正因為不相信現實是那樣,所以更需要相信理想該是這樣。越是不信,越要深信。
February 25, 2013
in《好 game 有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