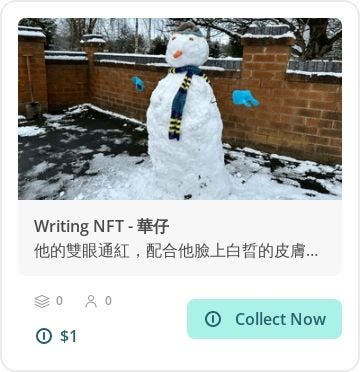曼城這幾星期氣溫掉到零度附近,下了點雪,雖比溫哥華的大雪雖然規模小得多,卻夠我們家樂上好一陣子。我和小兒子堆了個比花園圍欄還要高的大雪人,以甘荀和蕃茄仔當鼻子和眼睛,還替他戴上冷帽、手套、領巾。女兒的手藝比較優秀,做了兩朵冰雪玫瑰。但如此寒冷的天氣還是會影響生活的,首先我需要克服在寒夜半夜 3 點離開溫暖的被窩爬起床工作的巨大難關,不易,這星期便翹了一次課。為了貫徹節省能源的生活原則和省電費,我家少開暖氣,日間在家中工作坐得太久沒活動也真的感到有點冷。
今天難得放晴,我不顧霜雪導致的路滑,穿起兩對手套及兩條褲抵禦寒風,騎單車到鎮上一家餐廳坐坐,寫寫文章。Wetherspoons 被香港人稱為為「英國的茶餐廳」,食物價錢相對便宜,一個四磅左右包括飲品的套餐份量絕對足夠填飽一個成人的肚子,在冬天的時候暖氣開放,付一鎊半可無限添飲熱朱古力、咖啡和奶茶,簡直是我們這種對食物要求不高的窮L天堂。
我在那裏一邊呷著熱咖啡一邊寫作,見一名華人樣貌的男子在旁邊的桌子坐了下來。我覺得他很眼熟,他身高約六呎,厚厚的衣服也難掩那高高隆起的肚腩,面色非常白,卻非無血色那種蒼白,而是像年輕女孩那種白裏透紅,令那像塗了口紅一般艷紅的嘴唇十分突出。 我想起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來,脫口呼出了名字,他望向我呆了一呆,隔了半響也認出我來了; 世界如此廣闊,想不到竟然那麼湊巧在英國這不起眼的小鎮上跟故友重遇了。
你的樣子跟當年對比沒怎麼改變啊,只頭髮少了一些而已。他說。我摸了摸後腦斑秃那一塊頭皮,心虛地笑了笑。
他叫華仔,中學時我們曾經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自從廿多年前他離港到了澳洲發展以後,我們便再沒有碰面。記得踏進中一班房的第一天,一個靦腆的少年伏在我身後的桌子上,直到上課鈴聲響起他才抬起頭來。他的雙眼通紅,配合他臉上白晢的皮膚簡真有如一頭兔子;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那時得了紅眼症。之後我便跟坐我身後的華仔熟稔了,同時也以為自己戀上了坐我前方的女同學。
跟很多少年一樣,我們友誼的基礎建立在那些幼稚又深刻的戀情上1。那時他喜歡上一個住在我家附近的女同學,時常向我打聽她的動向。我們雖然在大埔讀書,我卻住在上水,要坐一程火車才能回到家;他為了跟我聊天 – 及當然也同時為了找機會見那女同學一面,有時放學後會陪我一起乘火車回家,邊走邊聊。那女同學的住所便在我回家必經之路旁的一個低層單位,每次我們一起經過那裏,他便像羅密歐在茱麗葉房間的陽台下站著一般,呆呆地期待着那女孩的心窗為他打開,然後無限次地失望而回。感覺有點自虐,但那卻是我們這種自命多情的少年所追求的感覺。那時我也會悄悄地坐在我暗戀的女孩住處附近的麥當勞,透過落地玻璃窗望向對面馬路大廈的大閘,期待可能有一刻她從裏面走出來,並驚訝地發現我正在為她揮霍寶貴的青䓤歲月。好些時候,華仔也會跟我一塊兒在那家麥當勞呆坐。 在單戀的戰場中,我們是親密的戰友。
我們都不煙不酒,卻會在傷感時一同倚賴流行音樂加深大家的癡情病況。那是香港人還會看「勁歌金曲」的年代,華仔特別喜歡譚詠麟,幾乎買了他每一盒卡式錄音帶專輯,而且總會很貼心地翻錄一份給我2,令我家書櫃中疊滿了 TDK60 的錄音帶盒子。我們藉着分享那些曲目傷春悲秋,開學時「愛在深秋」,打風時「暴風女神」,被拒絕時「愛情陷阱」,迷惘時「霧之戀」。然而不像張國榮把自己的輝煌永遠凝固,譚詠倫隨着年華逝去,如今已變得俗不可耐。我看着華仔的大肚腩,想著自己也快禿頭了,感到十分感慨。當年華仔可也是一個瀟灑的美男子呢。
那些年我有一部愛華 Walkman,是跟華仔一起在沙田新城市廣場一家店子買的3。耳機日夜緊貼着我的耳朵,拜華仔所賜的那些翻版錄音帶,還是譚詠麟的歌聽得最多。Walkman 除了讓我沉浸在幻想中的傷感裡以外,還另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把我從家中的噪音隔開。其實說是噪音也不太準確,吵鬧的聲音固然有,但大部份時間卻是更難耐的寂靜和肅殺。戴起耳機後,我彷彿躲進了一堵隱形的牆4背後,無視外間一切風波,進入自己的想像中去。環境越吵,Walkman 的聲量便被調得越大,以致有時脫下耳機後,耳朵和心靈都會有種短暫的朦朧感覺。
「你的母親怎樣了?」我問華仔。早在中學的時候,我便知道他的母親患上了癌症。
「她已經去世多年了。」華仔淡然說。除了愛情以外,我跟華仔重疊的經驗還有破碎的家庭。相比之下我的狀況沒那麼糟糕,最少父母是在我大學畢業後才離異的;但華仔的父母在他小學時便已出現婚姻問題。他的父親也像他一樣俊朗,在大陸工作時認識了一個女子,走在一起後便再很少回家過夜。華仔的父親曾經帶他一起見過那女子,當時他年紀還很小,印象中是一位相當漂亮的小姐,但可能是基於保護母親的本能吧,華仔對她十分反感。後來他們兩母子乾脆和他父親斷絕來往,二人相依為命,聽說他父親也不在意。可以想像年輕的華仔跟身患絕症母親在他父親的背叛後,日子有多難過。 當年我跟華仔同仇敵愾,咬牙切齒地咒罵那不負責任的男人;然而經歷半生後,我對於忠貞和責任這回事卻感覺不那麼理所當然了。
在華仔因為家事感到最難過的時候,我和他一起跟着一位很要好的老師到她深水埗的教會聚會。那位老師很年輕,當時也剛巧陷於戀愛難題中,有兩位男子同時向她展開追求,令她難以取捨。她竟和我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學生分享了她的掙扎。那時我們三人十分要好,周日常在教會聚會後從深水埗一起沿彌敦道走到尖沙咀,再在佐敦乘搭 81 號巴士回沙田,仍意猶未盡地在中央公園流連,談人生理想、信仰、家庭、感情,一直聊到深夜。後來這位老師辭掉教職到了政府工作,現在已經成為一名高級行政人員。多年後跟她偶然在大埔的街上重遇,發現她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心思單純的青年了,我們的話題不再圍繞信仰、理想或任何感情困擾,而變成討論事業發展、投資策略、和大灣區。 那次見面以後,我離開了香港,似乎也難有然後了。
後來我考進了大學第一志願的學科,華仔卻沒考上,尋找其他升學途徑,輾轉到了澳洲升學,再按當時的移民政策在那邊工作,落地生根。我整段大學生活都被家庭和感情困擾著,跟這位摯友漸漸疏遠5。婚後幾年我曾經遭遇嚴重的身心問題,雖然沒經醫生證實,但我覺得自己已有情緒病的徵狀了。那時我跟華仔已許久沒聯絡,但電腦上還有他的 MSN 帳號,便在線上跟他分享了我的困境。我只跟兩位最信任的朋友提起這事,他便是其中之一。我已忘了他如何回應,反正內容也不重要。那次通訊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們再也沒有通訊,後來因為我的電腦壞掉了,連他的 MSN 帳號也丟了,便連唯一的聯絡方法也失去了。華仔畢業後很低調,竟沒有任何中學同學知道他的聯絡方法,我想再找他也沒門,只好放棄。時間一晃竟已廿年,直至今天的重遇。世界和我的人生都已翻天覆地,我想華仔的人生也一樣吧。
我們在 Wetherspoons 聊了一會,他因為要趕赴下一個會議不能詳談,匆匆吃過飯後我們便交換了聯絡方法,然後道別。不知怎的,我覺得交換聯絡方法只是禮貌性的動作,其實大家不會再聯絡的了。可能因為現在彼此的距離,跟過往的親密落差實在太大了,像在友誼之間生出了一條無底深淵。又或者是因為隨著年歲漸長,我不知不覺竟失去了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了吧6。
這是一篇向《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致敬的虛構故事,因無法三言兩語表達清楚讀這本書時的心情而寫,若把這故事當成我的真實歷史,便會發現故事元素跟此書竟出奇地大量重疊,詳看下方註釋。視乎我的狀態,我還希望繼續以此主題多寫幾篇。
此篇主要基於《天》的第XI章「卡式錄音機」前半部,有關主角跟顯文的友誼部份。故事中無法覆蓋,卻也讓我共鳴的內容還有:林子祥的《究竟天有幾高》、對著錄音機作歌和傳情、喜歡歌劇的女孩、《春逝》、聽海的聲音。另,在這章節你會找到栩栩的耳朵是一對貝殼的原因。
期望結識同樣被這本書感動的書友,希望有一天能組個非官方讀書會,結交真正喜歡閱讀的朋友,尋找知音。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節錄
1 兩個孤單少年交換的心跡,必然是關於戀愛的苦楚。其實,我和顯各自經歷的還未算是貨真價實的戀情,但那已經是我們擁有的唯一值得自吹自擂的體驗了。我向他傾訴我對 Volvo女孩長達大半年的癡戀,他就向我剖白和聾啞女孩的一段令人遺憾的錯愛。
2 我把我的林子祥錄音帶借給他聽,後來又替他翻錄。雖然後來他自己也一一補購那些心愛的專輯,但他還是保存著封盒上有我的手寫歌名的翻錄歌集。
3 顯的第一部Walkman是我陪他去買的。
4 在今天耳機卻是對抗冷漠,維護自我完整的必要工具。我這樣說,是確認隱形的牆的正面意義。
5 可是,有些事情總會改變,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前那種親密的情誼總會成為過去。將來,只要心裡還會偶然想念對方,已經是他唯一的心願了。
6 栩栩,回想這件事,我才發現自己跟爸爸董銑和阿爺董富一樣,在成年以後便失去了交朋友甚或只是維繫友誼的能力。如果不是有家庭,我們在世界上幾乎是孤身一人。套用剛才的說法,我們也退進了一堵隱形的牆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