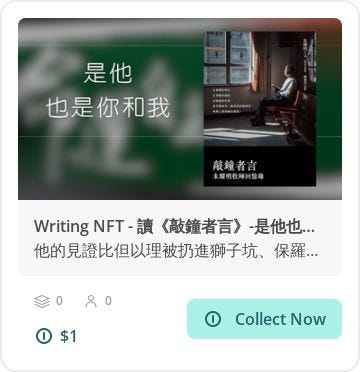好友來訪,見識到我那三歲小兒充沛的精力,及那滑稽的英文混雜廣東話的奇怪口音。她的眉頭微皺:「他可有學習中文的誘因呢?」老實說,我已有心理準備,小兒的母語將是英語。他或能聽明白廣東話,若能說幾句已令我喜出望外,不敢望他能讀中文書,更不會奢想他懂寫中文字了。
我不禁想起我的祖上。雖然太嫲嫲說的是台山話,但十來歲來港的爺爺說的卻是帶有台山口音的廣東話。我的爸爸輩說的是純正的廣東話,已不懂怎樣說台山話。我小時候也只聽得懂一兩句,自太嫲逝世後便漸漸地連那一兩句也忘得一乾二淨了。我上一輩至我忘掉台山話的過程,可能也跟小兒忘掉廣東話和中文寫讀說聽的過程一般無異吧。曾在附近公園遇到兩位三十來歲,於曼城出生的香港人後代,他們勉強能以帶口音的廣東話跟我交談,但他們的小孩跟我的兒子已在用英語溝通了。
除了教小兒唸幾句唐詩外,我沒有很刻意教他中文讀寫,也不是說我不重視中文,只是我的生活態度一向順其自然,在一些香港家長的眼裡我對孩子的教導可能甚至近乎散漫了。然而我總覺得學一種語言文化首重興趣,只要對廣東話和中文產生興趣的話,小兒便有很好的基礎兼容並包了。君不見河國榮唱《香港地》唱得多麼道地?
倒是我覺得追本溯源是人類的天性。人會好奇自己是怎麼來的,想從生理上初階地理解,也會想從文化歷史中進階地理解。文化歷史的學習是潛移默化的,難以一味量化地教導,填鴨硬塞或能湊效一時,長遠卻可能因反感而加速遺忘。我留意到孩子們似乎愛八掛父母的往事,於是偶然便談談自己的過去,也樂於有訴說的對象聊解寂寞。我跟女兒們說:香港的歷史其實很有趣,因為它跟我們這家人息息相關,能解釋為何我們今天走到移民英國這一步來。然後,我便從「香港從前是個小漁港」開始娓娓道來,邊說邊察看她們的臉色變化,若見她們開始兩眼發呆便打一個趣或縮短敍事篇幅,運用的技巧跟平日講牀邊故事時一般。
《敲鐘者言》中的香港故事
最近跟家人多談了香港的歷史,因我剛讀完了《敲鐘者言-朱耀明牧師回憶錄》。朱牧著此書時已近八旬,他的自傳可謂側寫了大半個世紀的香港,跟很多香港人的故事都有重疊之處。幼年時的窮苦經歷本令他憤世嫉俗,但基督信仰和遇到的善良伙伴改變了他,令他學會了悲憫、包容和勇敢。他對信仰的投入令他的自傳讀起來像一部基督徒見證集,我上一本讀的基督徒傳記已是年多前在教會圖書室信手拈來的《王明道文集》。
讀朱牧的自傳尤如在讀一部以近代香港為背景的小說,除了主角成長的情節,還有他身邊其他人物的成長情節。有趣的是我發現了好些跟他識於微時、日後在社會上發揮深刻影響力的名字,都是我敬重的前輩們。例如其中陳健民教授從在學時跟他合作爭取興建東區醫院,到支援愛滋病患者,直至最後一起帶領和平佔中,其戲劇性足以成為搬上大銀幕的電影劇本。
雖然朱牧自嘲說他的人生就是「成功神學」的相反,但他的經歷仍算是一種天助自助人的典型。一個連住處也沒著落、小學也沒畢業的小伙子立志當傳道人,並一步步實現夢想,為社會中的弱勢社群帶來祝福,故事何其勵志!他能捱到出頭天的原因除了因為上帝的眷顧和自身的努力以外,也可能跟當時正在急促發展的香港社會所提供給他的條件有關。我曾這樣跟孩子們比較現在和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當年香港人普遍的物質生活雖比現在要貧乏許多,但人心存希望,相信明天會更好,事實上社會也明顯地一天天在進步,政策和經濟一步步在改善;反觀今天的香港人雖然比過去那一代擁有更多,卻只感到絕望和沮喪。
我自小在教會長大,小學時便已決志歸主,因此讀此書時感受尤深 – 書中所引的詩歌《將你最好的獻與主》正是我少年時代的團契團歌,當年每次唱的時候還要站立以示莊重呢!雖然很多人都有唱過同一首歌,但有多少人能如他一般全然奉獻至最後燃燒成灰呢?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似乎都只是「成長」成一頭日夜為無意義的事物空轉的社畜而已。然而朱牧作為一位飽經憂患而最終能步進「收成期」的老者,竟毅然放棄穩定生活,為社會的福址一頭栽進「和平佔中」運動,要麼背後有強大的信念支持,要麼便肯定是個瘋子。他的見證,令本來對基督信仰已無甚期望的我又重燃了一點希望,因他不是遙遠的傳說中的偉人,而是近在咫尺的人物,且燃盡一生回應我故鄉的動盪。他的見證比但以理被扔進獅子坑、保羅下監、潘霍華被囚、馬丁路德遇刺更激動我心,因為他跟我的距離那麼近。
我城和我家的故事
回到跟孩子們講的香港歷史故事,我的版本日後或還會修改潤飾,但大概是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所以在英國這裡,是因為想追求自由的生活。自由關乎人的尊嚴,而那嚮往自由的心願曾經是香港人理所當然的希望,因為中英兩國曾於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向港人許下「一國兩制」的承諾,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然而這莊嚴的承諾,隨著自2004年中國藉人大釋法的粗暴干預起,到2014年的假直選決議,再到2020年荒謬的「愛國者治港」,已被徹底撕破了,中國和香港政府對港人治港的一切承諾都已證實是空話,加上它們各種濫權濫暴的行為,誠信已全然破產。
我們現在手持的 BNO,是在 1997 年前英國政府為安撫港人對被中國統治的恐懼而生的政策。為什麼當時香港人會恐懼呢?因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久的1989年,北京發生了六四屠城事件,中共以坦克輾碎許多爭取民主的無辜平民,令港人目睹專制政權的橫蠻可怖。自此以後,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 – 就是你們外公每周去踢波的那個公園 – 連續三十年每年都有悼念六四事件的燭光晚會,直至我們臨離開香港前,即 2019 年一起參加的那一次為止。
六四不是一件事不關己的歷史事件,因為它影響了我和我的家庭。我們父系的整個家族,除了我們這一家以外,全都在 1997 年前後的信心危機中移民外地了,這對當年我的原生家庭影響很大,我們因此失去了親族網絡的支援。我的原生家庭影響著我的成長,當然也影響著你們,因為我對自己家庭的想像或多或少都建基於對原生家庭的印象。而五年前香港發生的反修例運動的遠因也跟自八九六四以來的民主運動相關,而那年發生的事件直接導致我們決定舉家離開扎根多年的香港,來到英國定居。
十幾年前,我還是一個所謂的「大中華膠」,曾發過建設民主中國的夢,也曾相信香港能維持高度自治直至我退休老死,然而因我親眼目睹這些年政權的失信和野蠻而逐漸改變了想法。在經歷了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我醒悟過來了,不會再相信專制政權的空話。但我卻仍相信尚有持守善良與公義的香港人,我的餘生仍會繼續努力承傳優良的中華文化,因為那是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的關鍵。以上是我作為這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證辭。
小兒子還小,我當然不會跟他說以上這些他難以明白的事。然而若他對他父親的人生感到好奇,便必然會接觸到香港的故事和中國文化。我似乎只需繼續活得有趣,及重複演練我的香港故事便行,好響應朱牧和其他同道所敲響的鐘聲。
註:
-「是他也是你和我」是 1976 年電視劇「狂潮」主題曲的第一句,由關菊英主唱。起題時想起朱牧師的起點,也是近代香港的起點,也包括我的起點。
– 《將你最好的獻與主》是我成長教會的少年團契團歌,在此書第一章「孤子」中提及,聽著那些「唔啱音」的歌詞,想起當年很儍很天真的熱情,好有感。然而我不太認同朱牧引此曲而認為自己「不夠好」。那怕只是兩個銅錢,只要是自己最好的東西便行,而他無疑已獻上最好的了。
– 已逝世的河國榮唱過《香港地》,他的表演使我為香港的文化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