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虛詞無形的已讀不回介紹過周作人的《雨天的書》,本事出版又出版他的希臘文學翻譯作品,一時間這位經歷了民國革命、二戰抗日、共產文革三段風雲變色的時期的文學泰斗,在我離開學校三十年以後再次進入了我的眼簾。然而在留意到香港文學館和本事出版的訊息以前,令我先留意到周作人是因為對《少爺的時代》漫畫中的石川啄木這人物產生興趣,從而開始翻閱周譯石川的作品《石川啄木詩歌集》及《兩條血痕》,也順道讀了《少爺》。接觸《少爺的時代》的原因,又是因為讀了董啟章的《心》對夏目漱石等日本明治時代文學家的描述。
因此這段邂逅周作人作品的愉快經驗,可以說都是由董先生的作品所啟發的。謝謝。
周作人和老舍
說回周作人。他翻譯了不少日本文學作品,其中我特別喜愛《如夢記》,內容是作者小時候在鄉間跟爺爺、父母、鄰舍相處的趣事。可能由於自己也喜歡寫這種生活散文的原故,讀起來特別有感。
周作人在《如夢記》第一章的後記這樣寫:「在日本有過明治維新,雖已是過去的事,但中日兩國民如或有互相理解之可能,我想終須以此維新精神為基礎。」他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日子,在那裡取妻生子,對日本甚有好感,同時也憑他跟日本的這點淵源的熱情翻譯了不少日本文學作品。可是他身處民國、二戰到國共內戰的時代,中日兩地人民矛盾極深,他於是因在抗戰時受命留在北平,並接受日本傀儡政府的公職而在戰後背負漢奸的罪名而身陷囹圄。
同一時間,我在讀老舍的《四世同堂》,講的是國仇家恨,日本人在小說中的暴行尤如惡魔。書中有一叫「牛教授」的角色,醉心學術,深居簡出,不問世事;卻在受槍擊後因恐懼而接受了日本人所授的公職,為書中愛國者所不齒。這「牛教授事件」幾乎完全參照周作人的真實經歷。然而周作人雖未至於熱衷政治,卻絕非不問世事之人,至少他自有一套鮮明地回應時代的價值觀。這從他《雨天的書》這部字面標題只關風月的散文集中可明白地看出來:
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要自己遣責,自己鞭撻⋯⋯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剷除自己的惡根性,這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之復活。
《雨天的書-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他討厭專制,不屑劃一,拒絕盲從,崇尚自由:
我覺得中國人的大病在於喜歡服從與壓制,最缺乏的是對於一切專制之憎惡。 –
《雨天的書-托爾斯泰的事情》
他雖努力筆耕,且成果甚豐,但他對於文以載道改變世界的效用抱悲觀態度:
希臘有過梭格拉底,印度有過釋迦,中國有過孔老,他們都被尊為聖人,但是在現今的本國人民中間他們可以說是等於「不曾有過」⋯⋯至於期望他們教訓的實現,有如枕邊摸索好夢,不免近於痴人,難怪要被罵了。
《雨天的書-教訓之無用》
周作人多次提及他寫作的目的只為興趣,從他對社會現狀的悲觀及寄情生活細節的態度,我幾乎以為他是極端的犬儒了。然而想深一層,他仍會對社會和文化發展提出具體改善的論述,也是在嘗試以己所長改善現狀的一步,沒因為覺得做什麼事也毫無用處而不作為吧。
身處亂世的態度
若我也如周作人和老舍般,活在一個戰亂頻繁的動盪的時代,恐怕也會經歷他們那種自我質疑吧 – 讀書寫字、吟詩作畫、品茶聽戲,到底有什麼用處?雖然故城的情況未至於像他們當年那般壞,但我其實也曾這樣懷疑過人生。修文練武若不為光復世界的理想,有何意義?享受歲月靜好,怎對得起正為義受逼迫的同胞們?
對於如何生活於亂世,老舍和周作人的作品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老舍的《四世同堂》裡有一叫錢默吟的老者,一生謙柔,鍾愛藝術,享受寧謐;然而在全家被日本人害死後性情大變,生活再不修邊幅,放棄所有嗜好甚至家累,把抗日設為餘生的唯一目標:
「你們畫這些翎毛,花卉,和煙雲山水,為了什麼呢?你們畫這些,是為消遣嗎?當你們的真的山水都滿塗了血的時候,連你們的禽鳥和花草都被炮火打碎了的時候,你們還有心消遣?你們是為畫給日本人看嗎?噢!日本人打碎了你們的青山,打紅了你們的河水,你們還有臉來畫春花秋月,好教日本人看著舒服,教他們覺得即使把你們的城市田園都轟平,你們也還會用各種顏色粉飾太平!收起你們那些污辱藝術,輕蔑自己的東西吧!」
錢默吟,《四世同堂》第四十二章
主角祈瑞宣本來也是個不願開罪任何人的溫柔的青年,在經歷家園被侵掠者霸佔後的種種不公與荒謬以後,也生出不擇手段反抗暴政的念頭來:
「一個炸彈,把大赤包,高亦陀那群狗男女全炸得粉碎!」但是,他截住了這句最痛快,最簡截,最有實效的話。假若他自己不敢去扔炸彈,他就不能希望馬老太太或長順去那麼辦。⋯⋯他自己下過獄,他的父親被日本人給逼得投了河,他可表示了什麼?他只吐了血,給父親打了坑,和借了錢給父親辦了喪事,而沒敢去動仇人的一根汗毛!他只知道照著傳統的辦法,盡了作兒子的責任,而不敢正眼看那禍患的根源。他的教育、歷史、文化,只教他去敷衍,去低頭,去毫無用處的犧牲自己,而把報仇雪恨當作太冒險,過分激烈的事。
祈瑞宣,《四世同堂》第六十三章
以上的內容,若在一切以「國家安全」為橫行口實的我城中宣揚,已足夠構成入獄幾年的罪名了。
老舍透過筆下人物,表達出一種激烈抗命的思想,並輕看其他一切的生活細節、文化和傳統。這種把國家的命運放在遠高於個人之上的價值,卻不是與生俱來無端生成的,而是在經歷極端的苦痛和壓迫後生出來的。這跟今天被政權操弄、盲目仇外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一樣。
周作人也愛國,卻不像老舍像宗教信仰般狂熱。他愛國的理由老實得令人莞爾:
⋯⋯努力用人力發展自然與人生之美,使它成為可愛的世界,是很對也是很要緊的。我們從理性上說應愛國,只是因為不把本國弄好我們個人也不得自由生存,所以這是利害上的不得不然,並非真是從感情上來的離了利害關係的愛。要使我們真心地愛這國或鄉,須得先把它弄成可愛的東西才行。
《雨天的書-與友人論懷鄉書》
周作人不是個冷漠的人,相反他形容自己「神經衰弱,易於激動」,狀態還要跟今天很多同胞極為相像:
每天的報裡,總是充滿著不愉快的事情,見了不免要起煩惱。或者說,既然如此,不看豈不好麼?但我又捨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傷的人,明知觸著是很痛的,但有時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劇痛,保留他受傷的意識。
《雨天的書-山中雜信(三)》
半年前,曾經跟一位比我年輕十來歲的朋友討論當前我城青年的心境,他說很多年輕人不想再接觸時事,不再看報紙,寧願花時間追星享樂,甚至無意為長遠的將來打算。原因可能因為年輕人的感覺多較敏銳,易受刺激,反應激烈;若他們盡開五感接收現今我城的荒謬,會很容易超載而崩潰。於是在要繼續在此城好好生活的前提下,只好關掉耳目接收器,剎停對成長地方動情的衝動,再創造出能讓自己快樂地生活下去的條件來。世間固然也有心靈強壯,能面對酷刑仍處之泰然的,單看最近的案件便能見姣姣者,卻畢竟只屬少數。
我想,周作人的生活態度也跟上面提及的我城青年有點相似吧?
生活的藝術
周作人在《雨天的書》中強調的生活態度,是指每個人都可以、且應該定義自己生活中的樂趣與美善。當面對社會或潮流所給予的「幸福」定義時,或落在大眾所公認的「不幸」當中時,若能手握生活樂趣的話語權,便不會落得隨波逐流,也可瀟洒地面對得失,就如在一般人所厭惡的苦雨中興高采烈地玩耍的小孩般。
既知道大勢非一時三刻可變,個人的身心便更得好好照顧。一方面在能力範圍內持續發揮 – 周作人選擇了持續筆耕 – 另一方面在「苦雨」中發掘生活的樂趣,保持對世界的熱愛和好奇。掌握了自己的生活節奏,也有助不輕易隨世俗的主旋律起舞。這就是我讀完《雨天的書》後所領悟到的,周作人的亂世生活藝術。我認識的朋友中,有人學茶道,有人練瑜伽,有人練跑步,有人種田養花,有人多讀書,有人學烹飪;其中雖確有就此不問世事的,卻也有很多以更能致遠的節奏繼續實踐信念的,所謂坐直飲水鬥長命是也。此中關鍵在於時勢不就便保留實力,卻毋忘本心是也。
然而若慣了享樂安穩,難免容易死於逸樂。要做到生活靜好卻不忘本心,我有些實踐中的心得,雖未敢說一定能行,卻深信是有效的。
首先是追求精神上的滿足。暴政慣用的維穩技法不外是控制經濟資源以黨同伐異,此也非只暴政會行,實為社會的大氣候如此。人若被物質生活抓牢,吃慣了甜不肯嘗苦,開慣了車不懂走路,便再無自由實踐信念的條件,而被逼圍繞口腹眼目之欲空轉,並受掌握資源的人任意擺佈了。古今信仰,無論基督教還是儒、佛、道,皆教人檢樸修行,只為要人學會「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是也。這也是暴政總要打擊宗教自由的原因,因為當人追求的不是物質,轉而尋求精神上的滿足的話,便少了許多有效的維穩手段。所謂無欲則剛吧。
然後是培養低消費的興趣。對我而言,最便捷的便是閱讀和運動。讀書神通古人,連結同道,增廣見聞,俱佳;也能保有最大的自由度,因為不費多少錢又不限時間地域。另外運動鍛練身體的好處,不用我多說了吧。
如此說來,我是在推崇禁慾主義嗎?非也。看周作人在《雨天的書》中的看法,我深有同感:
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慾與縱慾的調和。⋯⋯歡樂與節制二者並存,且不相反而實相成。人有禁慾的傾向,即所以防歡樂的過量,並即以增歡樂的程度⋯⋯一切生活是一個建設與破壞,一個取進與付出,一個永遠的構成作用與分解作用的循環。要正當地生活,我們須得模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其嚴肅。
《雨天的書-藹理斯的話》
老生常談的就是要平衡。只是我會再三緊記,滿足欲望不是目標本身,美善才是;肉身的滿足並非最佳,精神的滿足才是。所以每逢聽到「要怎樣怎樣才算是生活」這種話我便甚警惕,恐怕自己不知不覺掉進物慾的羅網中去了。
倒過來說,若有保持寸心自由的信心,擁有和失去都能泰然處之的話,全情投入認真享受生活,又何妨?
提防民族主義的偏頗
這幾周我在幾本書所橫跨那一百多年的時光隧道中穿梭,更窺見不同時代中的人物內心。近代中日兩地人民的恩怨情仇互相糾纏之感,強烈地於腦中盤旋。我想起被專制政權操弄民族主義所製造出來的反智和愚昧,由是警惕潛藏於我內心深處,投射在我城的民族主義情結。因為當我讀《四世同堂》之時感受到的侵略者暴行和社會不公,不是來自書中的二戰時期的日本,而是投射於此時此刻正肆意欺壓我城同胞的專制政權。錢默吟和祈瑞宣對日本的憤怒和憎惡,跟我對賣港賊的憤怒和憎惡,同出一輙。
我為這番反省的結果而驚訝。
近日影響世界幾代人的日本漫畫家鳥山明逝世,傷感之餘,更體會到社群的親疏不只在血脈是否相連,更無關種族膚色,而在於信仰的價值是否共通。
推薦購書,坐言起行。全部經典電子書 4.99 美元 (約 38 港元)有交易!
虛詞無形 - 曾卓然說《雨天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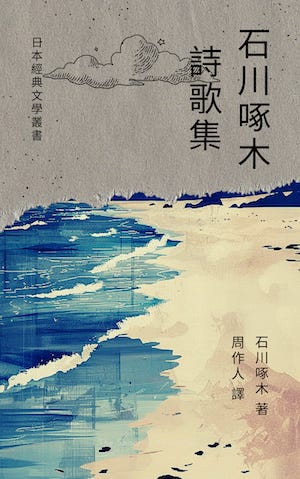
品住茶睇你呢篇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