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移居英國曼城時,曾嘗試尋找合適的華人教會。曼城比較有名氣的是位於市中心的曼城宣道會,用不著明查暗訪也早聽聞,只是我第一次到訪那裡卻純屬偶然。那時我們剛到埗不久,一家人乘巴士到市中心逛逛,打算認識一下這城市。路經 Oxford Street 一間專賣韓式食品的店舖附近時,來往行人中的亞裔面孔明顯增多,耳邊竟傳來熟悉的廣東話。我直覺地環顧四周,更加留意周遭景物。經過一個街口時朝左方望去,竟發現一個熟悉的標誌:由十字架、洗濯盆、油瓶和冠冕的圖案構成的宣道會會徽。原來曼城宣道會就在眼前。
熱鬧的曼城宣道會
我的心情有如他鄉遇故知,立刻跟家人走進了那教會的大門。教會位於一棟幾層高,外貌平平無奇的建築,室內空間並不寬闊,就如小時候曾上過的位於舊唐樓的教會般,然而小小的空間卻人頭湧湧。進去不久後,我竟碰到一張熟悉的臉,那是我在香港認識的某家機構的同工,原來他也到了曼城定居並在此聚會。更意外的,是遇到一位從前曾在我母會實習的傳道人,現時正在這裡事奉。那時他負責少年事工,與我這老餅不算很熟稔,但也互相認得。他們二人,是我在曼城街頭遇到的頭兩位認識的香港人。
於是我打算試著一家到這裡聚會看看。一星期後的周日,我們從家裡乘一小時的巴士,再訪曼宣參加主日崇拜。然而當我試著把兩個已屆少年的女兒帶到少年小組時,卻得悉小組已經滿額,她倆當日不能參加,只能隨我們參加大堂崇拜。我按要求把她們二人的名字登記在「候補名單」中 — 這實在是新奇的經歷,因為我從沒試過參加教會聚會是要進候補名單的,從前在香港教會時若有新朋友來,舊人寧願站著也要留住他們的呢!曼城宣道的人流何等興旺,及事奉人手和資源何等緊絀,可見一斑。
然而兩個女兒這年紀,不喜歡正式崇拜那種較為樸實的模式,加上整個小禮堂擠滿了人,空氣異常悶熱,更令她們如坐針氈。過了一個多月我們還沒等到能進團的消息,既然小組名額爆滿了,兩個女兒也也順勢停止回教會,她們已屆少年,我也只好尊重她們的意願。事實上我也覺得週日來回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也真有點累,曼城的巴士在週日還要特別不可靠,經常突然脫掉一班,動不動要白等半個小時。於是我們就此打消了到曼宣聚會的念頭。
熟悉的旋律
後來我們決定嘗試到家附近的本地人教會聚會。女兒們拒絕到英語教會聚會,於是我們過去十多年一家人週日一起上教會的生活習慣也正式畫上句號。過去兩年的教會生活就只有我兩夫婦跟小兒子三人一起渡過。
教會和我家只相隔步行十五分鐘的距離,建築風格較接近現代,不像區內其他動輒上百年的老教堂。後來知道離我家 30 分鐘步行距離有另一所 700 年歷史的老教堂,古舊的石牆、紅磚、鐘樓、尖頂、彩繪玻璃,竟仍在運作中。我雖對那教會甚為好奇,但最後還是選擇了在離家更近的那家教會聚會。
別說我從沒參加過英語教會聚會,過去三十年甚至一直只待在同一家教會中,即是那種群體中所有人都認得的 "old seafood”;所以現在步進陌生環境時心情不免有點緊張。我從小在教會長大,能把聖經目錄、使徒信經和眾多經文背頌如流,但換成英語後,竟連書卷的名稱也唸不出來,更別想開口以英語祈禱了。我發現過往那種習慣了的教會生活模式,甚至連說話的詞語和句式,原來都內化了在我血液中,變成了習慣甚至本能,現在卻反倒成為適應新環境的心理障礙了。我跟太太每論及此事,都覺得不妨擁抱這嶄新的經驗,算是跳出舒適圈吧!
然而我們不是完全從零開始的。香港教會跟遠隔重洋的英國教會的信仰內容,核心是一致的,部份儀式也是相似的。第一天聚會時,我唱的第一首歌名剛巧是 “A New Commandment”,那是我和太太少年時唱過的英文詩歌,歌詞基於一節經文:「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便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旋律響起,心中冒起莫明的感動,從少年時代直至今天的信仰經歷竟一幕幕如走馬燈般在腦海浮現。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unto you
That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That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By this shall all men
Know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have love one to another
打開那本英文詩歌集,單看歌詞,我一首歌也不懂;但旋律一響起,卻發現不少其實是從前唱過的《生命聖詩》之類的古舊詩歌的英文版。因為這些熟悉的旋律,我感到較為安定和輕鬆了。
最幼小的樹苗
英國教會的信徒老齡化問題,比香港嚴重得多。雖然不是正式的統計數字,但據我觀察我加入的這家本地人教會大部份是退休人仕,60-80 歲佔大多數。我和太太雖都已步入中年,在這裡卻竟成了最年輕的恆常會眾之一。小兒子更是這裡最年輕的小孩,剛來時他只有三歲,還未懂說話,主日學課堂大部份時間只有他和另一位 10 歲左右的英國女孩參加,偶爾會有一、兩位小同伴,但都不是很穩定。將心比己,那些主日學課程對那女孩來說太顯淺和幼稚了,我想很快她便會覺得無聊 — 可能現在她已有這感覺了,只是因為慣性和家人的原因仍待在這裡而已。每念及此,我都不免為那女孩的信仰、和教會的青黃不接而擔憂。
尤其相比曼城宣道會的興盛,這邊明顯是荒涼得多了。然而,可能也因此他們更需要我們的貢獻。
可能由於教會的小孩不多,小兒頗得眾人的喜愛。有時他會在聚會中搗蛋,例如發出擾人的聲音、亂丟東西、甚至還曾打破了小禮堂聖壇上的一個花瓶。他在一眾顫巍巍的公公婆婆之間奔跑穿梭時,常令我夫婦倆捏一把汗。可能由於新移民的身份,我對自己在外的言行舉止格外謹慎,生怕不小心開罪了別人或引起煩厭,也因此對小兒的騷擾行為顯得緊張。後來發現除一位教友曾對小兒某些過度活潑的行為發過幾句微言(她是負責管理場地的)以外,其他教友都對他挺包容的,可能是我過慮了。
傳統還是慣性?
本地教會聚會的形式跟香港教會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幾乎所有聚會的祈禱辭和經文都已定好,每年按節期安排,會眾跟著頌讀。這跟我從前聚會中的隨心禱告的形式有極大差別。從前我很抗拒唸禱文,認為那不是發自內心,更遑論按聖靈感動的「唸口簧」,覺得對連結上帝毫無意義;然而現在這唸頌的傳統卻降低了我投入英語崇拜的門檻,聽不明白的話還可以跟著唸,唸得多便開始慢慢理解了。
唸禱文的傳統應該是承襲自天主教,然後在英國還可追溯到十六世紀的 Book of Common Prayer。當時會眾大多目不識丁,本來都要靠教士代為祈禱,但有了禱文,會眾便能較容易掌握如何自行祈禱了,當時來說是重要的進步。我固然未至於目不識丁,但在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之下,這種規距的崇拜模式確實讓我較易先踏出半步融入群體。然而,這裡的人不少已這樣聚會幾十年,經歷了那麼長時間,內容一式一樣的敬拜不會變得慣性因循嗎?我反思儀式跟生活的關係,愈來愈明白人們因著先天或後天、內在和外在各種因素,對傳統儀式和象徵符號的倚賴是怎麼一回事。我想,人們傾向倚賴慣性,安頓情緒,簡化概念,目的只是為更省力地生活。這種倚賴的傾向若要分對與錯,便是在傳統的原則受挑戰的時刻;若放棄原則堅持傳統和慣性,便有如聖經中的文士和法利賽人。
我好奇,若這教會中的叔叔姨姨們面對我們過去幾年的處境,會怎樣以信仰的原則回應。
好書推薦:《極權下的人性:文學中的集中營與惡托邦》
最近在讀這部書,非常好。身處英國經常接觸到二戰的歷史故事,方知自己過去對那場災難的了解十分片面,尤其對德國的集中營和蘇聯的勞改營的事情,更只是停留在電影畫面的模糊印象。我目前只讀了此書頭三章,可能因為訊息量很大,我不禁翻來覆去重讀了幾遍,對描述當時情境的文學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現代的極權社會,在方方面面以高壓手段把異見者「非人化」,以權力宣揚明顯的謊言直至群眾麻木等等手段,雖然跟勞改營有程度上的分別,背後的理念卻如出一轍,令人愈讀愈心寒。
大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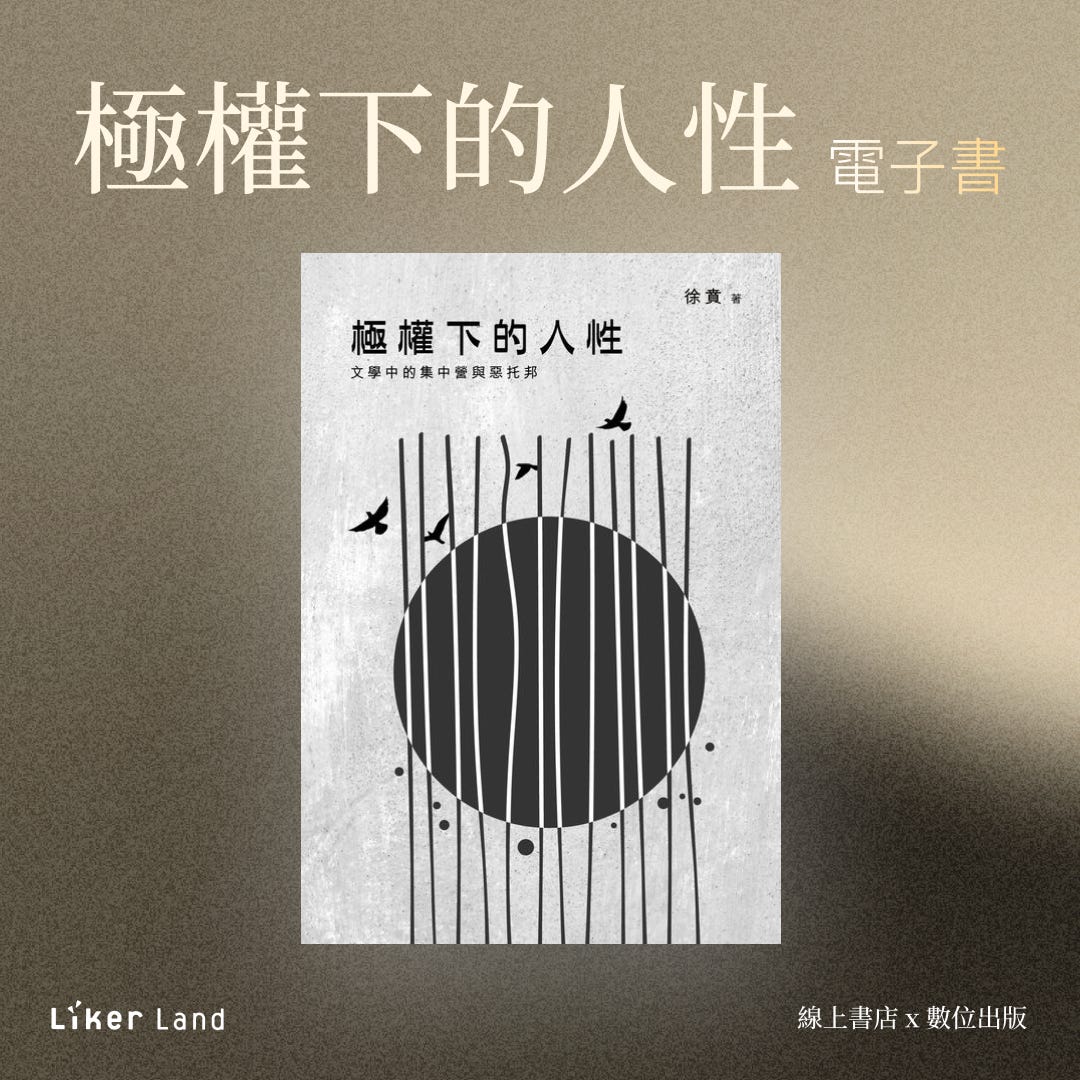
剛從教堂出來就看到這篇,老齡化一樣嚴重,我和你剛好相反,最初了解基督宗教全是從外語聖經,禱文,儀式開始,後來有人送我一本中文聖經,打開直接傻了,找到對應翻譯時往往驚訝於怎麼會那樣翻譯